时期当然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秦晖历史的不同面相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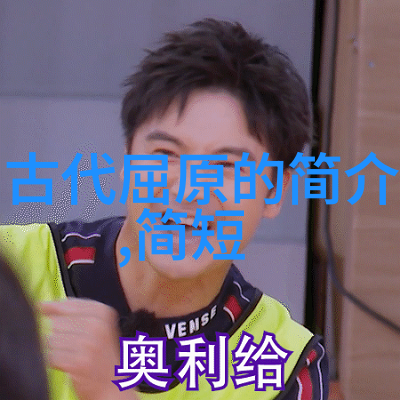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我对经济的论述后来招致许多批评。值得辨析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战争的破坏不能与制度评价分开,时期战乱多,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必有的结果;二是说我上述的“时期最高水平”包含了伪满时期的东北,而那时东北的建设是日本人搞的,不能算在的账上。
对于第一点,我前已说明,那时国内的“乱世”和乱后的太平一样,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而国际上的大战也席卷了不同制度的国家。同样是帝制时代,你不能以“永嘉之乱”证明“旧社会的黑暗”而以“文景之治”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吧?如果说中国遭日寇侵略是“旧社会”必有的;苏联遭德国侵略,难道就是必有的?沙俄帝国崩溃导致惨烈的战乱,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过错;可苏联解体导致的混乱,又是谁的过错呢?
其实,治乱之别在各种制度下都存在,倒是治乱之际的“剧变”,无论追求什么制度,对于“变后之乱”都有“事件”上的直接因果联系(至少是逻辑学上的“前后件”的联系)。有人(例如萧功秦先生)因此反对一切剧变,追求的十月他反对,追求“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变革他同样反对,追求宪政的辛亥当然也在他的反对之列,这个逻辑倒是彻底的。前面已说过,我不赞成这样肤浅的反对。但是就“直接因果”而言,你不能不说他们的反对事出有因。
但有趣的是,我的上述批评者并不是萧先生那样的人,而是一批“左派”朋友,他们赞成,包括辛亥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鼓吹,却又把建立的说得一团漆黑,并且绝对不考虑“乱世”的因素,而对后果作本质性的全盘否定,这哪里还有一点逻辑呢?
我当然不否认时期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即辛亥“尚未成功”的那些体现,以后我还会详加论述。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对于第二点,首先从比较统计的对应性来讲,把时期的全国经济,切掉东北这一块,来与以后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经济作对比,这合理吗?要知道东北并非无足轻重,它作为全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在1949年前后,直到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闹掰、开始搞“三线建设”之时,并无变化。先把这一中心拿掉,再来反衬合并这一中心后的“成长”,能符合客观实际吗?而且,过去用作比较基点的1949年数字是包括东北的,为什么“时期中国”的最高年产量却要去掉东北?
尽管1949年时东北工业因抗战末期与内战的破坏,尤其是苏军占领期间的疯狂拆卸,已成废墟,但正如德日战后的情况那样,战争能摧毁工业的“硬件”,“软件”即工业文明造就的人文资源仍在。1950年代,东北在苏联援助下能迅速复兴,与此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对1945年前东北的工业化成果,新中国也有所继承,这些成果怎能记在日本人名下呢?
其实,前苏联的发展成就统计,就有个比较基点,即“今(苏联)疆域内1913年”的产值,因为1913年沙俄的疆域与后来苏联的疆域有不小的区别,但只有相同疆域内的前后比较才有说服力。类似地,苏联统计战后经济成就的基点,是“今疆域内”1940年的数据,尽管苏联战前战后的版图有了较大的变化。1913年的沙俄,囊括芬兰与波兰的大部,但后来的苏联不包括这些地方,把它们也算进1913年的数据里,就会压低苏联的成就。
同样的道理,1931-1945年间,东北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但如果统计“年间的中国”时刨去东北,当然就会使“1949年后中国”的相对增长率失真。
的确,年间的中国取得的成就,不能都记在当时中央政府的账下,如果那时一些领土(例如东北)不归它控制的话。但是这些地方的成就,难道就可以记到日本人的账下?且不说东北在沦陷前,工业就有一定基础,就算没有,如果殖民地的成就都要记到宗主国账下,是不是“半殖民地”的成就,宗主国也要切去一半?而像印度那样,独立前全境都是殖民地(如同1945年前的东北),是否所有成就都要记到英国人名下,全部经济都切割出去?如果那样的话,独立后印度经济的增长率岂不是变得无穷大了?
从另一方面讲,当时不仅东北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其他一些省份的地方势力,也不同程度地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是不是这些地方的经济都要切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当时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上海等地,倒是那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仅以这些地区论,岂不“美化”了?再说,假如中央政府控制不了的地区,经济成就就与“”无关,那些地区的黑暗、贫困为什么就与“”有关?中央政府不能窃中国全境的经济成就之“功”,为什么它却应该负中国全境“万恶旧社会”之责?
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显然,我们比较的“年间中国”是个时代、区域的概念,不是政府的概念。如今中国统计覆盖的区域在年间的状况,是衡量今天我们发展成就的参照,而这一区域清代的状况,又是衡量年间发展的参照,也是我们评价辛亥的参照。这类参照体现的“发展成就”(通常用增长率表示),本身是个客观事实。至于这个事实的形成机制以及这个事实是好是坏、谁付代价谁获益、谁该居功谁该问罪,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是该区域人民付出努力和代价得到的,无论这个区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独立国土,也无论该区域的统治者是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反对派还是外来殖民者。香港1997年前殖民时代的繁荣,是港人(中国人)的骄傲,不能全由港英当局乃至英国人居功,为什么日据时期东北的工业化,就该全部归功于日本人?而统治者如果不择手段地追求“发展”,无限度地役使人民造成苦难,特别是,如果这种“发展”又是为统治者自利,而不让人民分享,那么发展速度再高,统治者也应当被谴责。但同时,这种发展为后来历史阶段的新发展提供基础,也是客观事实,不能无视事实,而硬说后来的成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
因此,承认当时东北的工业化,是年间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和后来中国工业新发展的基础之一;同时谴责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两者并不矛盾。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是个事实,这工业化出自中国人(东北人民)的血汗,我们无需“归功”于侵略者,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以这种殖民地条件下的工业化为自豪(尽管其成就可观),原因很简单:发展和工业化并不是可以不论代价的。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工业化,不可取;以牺牲为代价的工业化,同样不可取。
其实,我所引述的年间中国不少主要工业品(大都是重工业品)的最高产量,确实是出现在抗战期间,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东北等沦陷区。东北铁路密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年间,中国轻工业品、消费品的最高产量,则出现在抗战前夕,生产中心也在内地。一般公认,年间中国的整个GDP最高年份,也是在全面抗战前夕的1936年,年间中国人民生活相对最好(乱世中应当说是最“不坏”吧)的年份,也是1936年。经济在乱世中的亮点,主要也就在这里。
显然,年间中国的重工业,不是没有发展;发展的重心在殖民地东北,也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当时,落后国家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往往是作为外国人势力范围的“开放地区”,香港和各地租界就是这样。这也是客观事实,东北并不例外。但是,东北不同于香港之处,在于这里的重工业,是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因此,一方面,低附加值基础工业品相对搞得多,而高附加值消费品搞得少,导致重工业品最高产量年份与GDP最高年份明显不同步;另一方面,在重工业品最高产时,老百姓的生活却陷于苦难深渊,前面谈到的侯杨方等人的人口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正是日本人该谴责的地方之一。
逆差中的繁荣:全球化中的经济
关于经济,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背景。
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形成外需拉动模式,外贸从1980年代的“逆差时代”,历史性地转为顺差时代,而且顺差急剧增加,成为“中国崛起”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经济史研究者对清代的高顺差也表现了极大兴趣。清前期外贸中,“只卖不买”导致外银大量流入,得到高度评价,“白银时代”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两个说法叠加,使得“顺差崇拜”广为流行。
而时期的经济一方面国际性(也就是所谓“半殖民地”性)较强,另一方面外贸逆差之大,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按“顺差崇拜”的观点,这是否表明:经济是历史上最差的呢?
其实贸易既非赠与,总是要有交换的。所谓顺差,无非是别人需要你的产品,但别人的产品你不需要,于是别人只好使用某种特殊支付手段。明与清前期,外国量购买中国商品,但外国一般商品在中国却卖不动(所谓“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于是他们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据说这就证明了我们经济的先进。西方商人后来想出损招,用鸦片替代白银,由于鸦片上瘾后欲罢不能,中国就不能不接受这种替代,导致白银由流进变为流出,中国于是就衰落了。
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问题:西人用鸦片替代白银,来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这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并不会减少我们的GDP。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仅仅讲GDP,假如白银流入时代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代替白银后怎么就不是了呢?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
从1891至1895年,即使包括鸦片进口在内,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仍然从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万海关两,年均增长26.4%之多。而如果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9页),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笔者据前引陈争平书数据推算)。
换句话说,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外国(主要是列强及其殖民地)每购买100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有近30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与清前期的区别仅在于,这些特殊支付手段以前主要是无害有益的白银,现在则主要是有害的鸦片。但是西方的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则与前毫无区别——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这种“西方无法与中国竞争”的“劣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似乎还明显增大了!
也就是说,如果按“顺差崇拜”的逻辑,中国经济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从而持续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而置西方于“边缘”,而且鸦片战争后也仍然如此(甚至更强了)!如果像有些人所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靠“顺差优势”,GDP能占全球三分之一,那么甲午时这一“优势”更大,GDP又该占多少呢?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比西方领先,已经很惊人了,要说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领先甚至更加领先,这能让人相信吗?!
然而到了甲午以后,如此辉煌的强势,不知怎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建立后,更加明显。而且在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这种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的大量增加引起的。1896-1936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18840万美元)。(陈争平前引书,51-52页)西方工业品“忽然”变得有竞争力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甲午以后中国的外贸逆差时代,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尽管是被动地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就前者而言,中国的逆差,反映了其孱弱的产业,完全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因而处在可悲的依附或“边缘”地位;但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此前中国的“顺差”,丝毫不反映中国的强势,只表明那时的中国开放度尚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是十分可怜的。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国人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
而此时的“顺差”转逆差,则体现了此种状况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地)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的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还有,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72-73页),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的。
历史的先声
而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
迄今为止,据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笔者据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l. 1, New York, White Plains: Kraus International Pub.1989. p.232所载数据推算]。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即便按麦迪森的统计,在1820-1890年这7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据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109-144页数据推算)。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慢。还应该指出,经济的统计,与今天相比,尽管仍然粗略,但毕竟已经有了海关统计、农商调查等近代数据可依,比起“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三分之一”这类完全依靠间接推测的结论,要可靠得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上述增长并不难理解:中国本来非常落后,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也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弱势。但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时期,“顺差优势”更加扩大,年间再有这样的增长率,中国怎么还会有落后的可能?
中国到底曾经有一天“落后”过吗?晚清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痛心疾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以图拯救的民族危机,难道根本就是庸人自扰?
显然不能无视常识。我们只能反过来想:年间,这样的增长率尚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能说明此前落后更甚!包括明清的“顺差时代”,体现的也许并不是我们的“优势”,而恰恰是劣势?
我国历史上,汉唐宋元历来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国家,但与强盛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对外贸易都是“逆差”。这种“逆差”,在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美国类似,实际上是一种“购买力优势”的反映。当时,中国的货币,由于逆差而流出海外,成为“国际货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今天的美元。恰恰是在明和清前期,情况倒了过来:中国出现“消费劣势”,由于“只卖不买”,导致外银流入,这正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由盛转衰的体现。
当然,“顺差优势”说不成立,并不等于“逆差”就是优势。甲午以后尤其是时期,工业化启动、投资品进口,导致大量逆差,这确实是中国工业弱势、缺乏竞争力的反映。但是,与明清“消费劣势”不同的是,工业化的启动和投资的活跃,为改变弱势提供了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过来的:改革前,中国闭关自守,进口极少,一直有少量顺差,但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糟糕,是众所周知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门户逐渐开启,乃至接着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发展加速,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旺盛的建设需求,又导致投资品进口大增,因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仅见的一段十多年的大逆差时代。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甚至超过1949年后三十多年的顺差总和(黄建忠:《国际贸易新论:现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探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4-5页)。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大逆差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是此前那个“顺差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时期的大逆差,与时期的逆差,有一点类似,即都与工业化投资拉动有关。正是在此一发展的基础上,从1990年起,我国凭借“逆差时代”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和突出的低成本优势,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起飞道路,开始了迄今仍在延续的大顺差时代。
可见,即便是在现当代的中国经济进程中,简单地说顺差时代一定就比逆差时代好,也是大谬不然。经济的“逆差时代”,相比甲午时的“顺差时代”,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尽管由于战争破坏,延宕了工业化,没有出现我国1990年代的那种转折,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先声”吧。
选自秦晖《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
标签: 已经证实朱元璋是朱温后代 、 简短励志小故事 、 屈原的故事讲述了什么 、 古代屈原的简介 、 中国第一个 叫什么



